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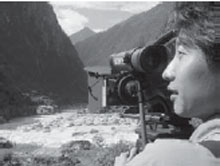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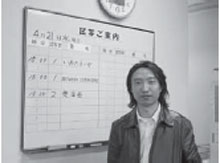
一次难忘的心灵之旅,与壮壮同走《茶马古道》
数字电影记录片《茶马古道-德拉姆》近期在国内院线通过胶片版进行了发行上映, 取得了很好的社会反响和票房成绩。回想自己一年多的拍摄制作经历,许多往事难以 释怀。
田壮壮作为知名的资深电影导演,一直对年轻一代的电影人倾注了很多心血。而且近 年来特别对数字电影技术抱有浓厚兴趣。去年(03 年)4 月份,正值非典肆虐北京。 壮壮从云南打来电话,约我去拍《茶马古道》,并且决定采用数字拍摄。能得到这样 的机会令我兴奋不已。怒江大峡谷一直是我梦想的地方,而且能够和壮壮、王昱一起 合作、朝夕相处,对我来讲是一次难得的梦幻之旅,又将是一次难忘的心灵之旅。
怒江大峡谷地处西南边陲,距离北京约5000 公里,距离广州约3600 公里。如果采 用胶片进行拍摄,往返接送样片一次大约需要两周的时间,而且胶片的保存、运输具 有相当大的风险和困难。对于《茶马古道》这样艰苦和难得的拍摄任务,如果出现损 失将是无法弥补的,所以田导演最后决定采用数字方式进行拍摄。当然时至今天,从 《茶马古道-德拉姆》最终用胶片版进行发行上映的结果来看,当初的决定是正确的, 以至于影片在纽约翠贝卡电影节放映拷贝时,众多外国记者和同行被影片的美丽影像 所折服,完全以为这是一部用胶片进行拍摄的电影。
当初在选择数字摄影机时,我对松下公司提供的AJ-HDC27F 进行了仔细研究,它的 小巧机身、高灵敏度和CINEGAMMA对我颇具吸引力,但是由于DVCPRO-HD的记 录格式对于记录带后信号的压缩比太大,影响了带后图像的分辨率,以至于我最后放 弃了它。其实Sony公司的HDW-F900也存在一些问题,我在拍摄《冬至》时经常向 Sony 公司的亚明、建军抱怨。好在去年四月,为了筹拍《茶马古道》,Sony 公司特 意从日本调来一台刚刚完成的F900 的升级版(就是现在的F900H)。通过对比,我 发现新的升级版对CCD的驱动电路进行了改进,为影片赢得了宝贵的亮部层次。事 实证明这个选择也是对的,因为在磁转胶的过程中,分辨率会有所损失,如果不是选 择了1080P,清晰度的损失会更明显。
为了保险起见,我们出发时还是带了两台F900,以备万一。但是机器一直工作正常, 经受了高温、高湿和长途颠簸的考验,并没有出现万一。现在让我遗憾的是当时为了 减少旅行负荷,我们尽量精简了设备器材,没有带上蔡司的DigiPrime定焦镜组,只 带了Angenieux 11.5 × 5.3 HD T1.9-2.5 的电影变焦镜。通过放映拷贝可以看到有 些画面还是焦点偏软,锐度不够理想,令我至今心存遗憾。
王昱是我的校友学长,也是年轻一代电影摄影师的优秀代表。他给我的印象是思想敏 锐、情感丰富,具有很高的艺术修养,在摄影师中并不多见。这次拍摄《茶马古道- 德拉姆》我与王昱联合摄影,对我来讲是一次不可多得的学习机会。自然在拍摄间隙、 露营途中少不了要讨论一些影像与电影的问题。当然我们很少讨论技术问题,更多的 是讨论创作观念和电影态度。
在谈到数字摄影手段的技术演进对传统胶片摄影手段的影响时,我们的看法也是这 样:数字与胶片作为传达影像的工具是平等的,但是传达的过程是有区别的。胶片影 像会更加直接,更为感性,由于模拟的感光材料和化学工艺的不确定性,会给最终结 果带来某些“即兴”的成分。而数字影像会比较理性和间接一些,“所见即所得”的 数字特性也使得最终结果变得精确可靠而无“悬念”。所以我认为今天的电影摄影师 应该掌握和精通不同类型的影像技术手段,针对不同的创作内容和创作方法,完成最 准确而富有意味的影像传达。
当然技术并非不重要,它是一切影像创作的基础。特别是运用数字手段进行电影摄影 创作时,过多的技术环节和现有设备的局限甚至是缺陷,给摄影师带来了更大的技术 难度,要付出相当多的精力来解决。我所坚持的原则就是在拍摄现场,一定要做到无 缺陷采集。简单的说就是不能虚焦点、不能丢层次、不能出噪波。一旦出现这些问题 在后期是无法弥补的。这样的要求看似简单,其实很难,要保证整部影片都不出问题, 就更不容易了。因为在8米以上的大银幕上进行检视,任何细微的缺陷,都将被夸大, 让你无法忍受。
所以在拍摄现场,我自制的焦点检测图标,一直是形影不离。镜头的后焦点我会经常 检查,一天会有三次或更多。监视器也要经常校准,为了保证分量信号线不出问题, 我又专门定制了两条冷压线。这一切都是要保证设备处于最佳状态,没有系统误差。 关于摄影机的现场调整,也基本上是每个镜头都要对PAINT 菜单内的各项参数进行 调整。确保每个镜头画面的亮度间距以最适合的比例压缩或扩展到CCD全部可用的 动态范围之内。也就是说根据每个场景的照明条件、亮度间距、影调气氛的不同,每 个镜头的景别、角度和构图的不同,通过改变黑电平、黑GAMMA、主GAMMA、KNEE 的拐点和斜率等,定制出一条最匹配的GAMMA曲线,将千差万别的输入电平,经过 调整合理分配在710mV 输出电平的动态范围之内,做到既不损失景物层次,也不浪 费CCD 有限的动态资源。
根据导演意图,我把云南流域段(丙中洛)和西藏流域段(察瓦龙)在色调上进行了 区别,前者主要突出湿润、清灵,而后者强调干燥、炎热。关于不同地域的主色调, 我主要在用户矩阵里进行分别设置。当然要注意保持场景间的协调关系,过度调整会 出现视觉失真的问题。在保证现场采集的画面没有缺陷,比较完整的前提下,我更喜 欢把色调调整的工作放在后期的电子配光和光学配光来完成。
《茶马古道-德拉姆》的后期制作长达10 个月。分别在日本的NHK、Sony-PCL 和 EXA公司制作数字版的画面和声音部分;在北京华龙公司和日本东京现象所完成了胶 片版的输出和洗印;在捷克的SONO recorders公司完成了音乐混录;在北京电影学 院完成了胶片版的声音编辑和初混;在北影录音车间完成了胶片版的终混和数字杜比 的编码;在东京的日活电影公司完成了声音转光学;在北京洗印技术厂完成了发行拷 贝。这是一个涉及众多公司、众多技术设备、众多制作人员的复杂的制作工程。我有 幸直接参与承担了这一庞大而繁杂的后期制作全过程,丰富了技术经验,也对目前世 界范围内的数字电影制作技术有了比较全面的接触和了解。
在此之前国内还没有数字转胶片的成功先例,田导演从影片的筹备开始就要求把胶片 版发行作为最终目标,我也是按照这一要求严格的控制拍摄制作中的各个技术环节。 去年(03年)10 月份,《茶马古道-德拉姆》的数字版在送审电影局时获得了一致好 评,制片技术处的郑景泉和丁立两位处长认为数字版的品质很好,为数转胶的制作工 艺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建议我们尝试把《茶马古道-德拉姆》转成胶片版,并且一定 要小心谨慎不能失误。在此之后,我们在澳洲、日本、泰国、台北和中国选择了几家 具有ARRILASER制作条件的公司分别进行了样片记录实验。对各个公司的LUTs曲 线参数和冲印条件进行比较,各具特点也都存在问题。直到今年春节过后北京华龙公 司在ARRILASER 上安装了CMS软件系统,记录的样片才让田导演初步满意。
我认为CMS的贡献在于数字影像经过ARRILASER记录在胶片上其色彩基本上能接 近CRT显示器的色彩效果。在过去数字的CRT显示系统与胶片的银盐乳剂两大系统 之间的色域空间如何定量转化一直是困扰我们的问题,现在可以说得到了初步的解 决。但是在实际操作中问题仍然存在,比如我们虽然严格控制了LAD 灰板的RGB密 度,但是在冲洗拷贝时,还是出现了不少色彩偏差,仍然要依靠光学配光进行最后的 色彩校正。可见模拟的化学冲洗加工工艺,国内或是国外都存在一些不可控的因素。
再有就是在转胶的过程中,清晰度的损失让我很痛心。经过数转胶清晰度的对比实 验,我发现:数字信号经过ARRILASER 记录到5242 原底片之后再经过2383 印制 成拷贝片,清晰度从720 线下降到650 线左右,分辨40 线对时就已经很勉强了。毕 竟胶片是有颗粒的,接触印片也会损失细节,这些都无法避免。看来数转胶还是存在 一定问题,从长远来看,数字发行与数字放映才是解决数字电影的根本方法。
《茶马古道-德拉姆》已经在国内四个城市上映了,可以说这部影片是中国数字电影 从探索阶段走向成熟阶段的标志。回想这一年多来的制作经历,虽然历经艰难,遭 遇很多挫折,但是在看到影片尾声,丙中洛的漫漫白云弥漫于天际之时,在我的内 心深处依然是无法抑制的喜悦和幸福。
二零零四年七月于北影

